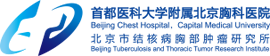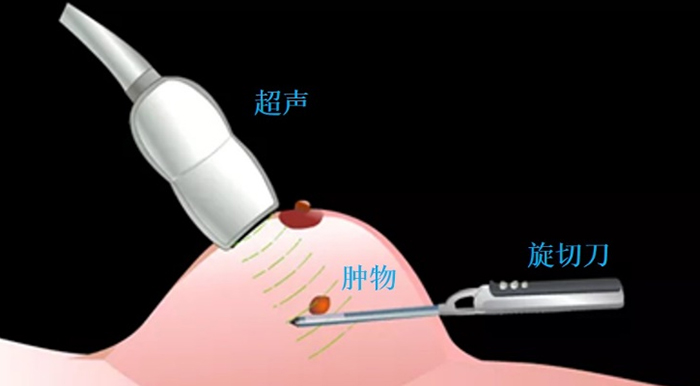百姓聚焦
【医学人文】彼此信任,是创造奇迹的前提
北京胸科医院
医患互助中的信任纽带
导航
彼此信任,是创造奇迹的前提
“张主任,小波这回怕是挺不过去了,去ICU治疗,听说全身要插好几个管子,我不想再让他再受罪了,不抢救了,您说我这个决定对吗?”
学会识破“保护色”
面对病痛折磨时,他们内心真正需要的,还是那一份理解、关注与陪伴。
本篇作者

张静,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急诊科主任,主任医师,从事结核病诊断及结核病危重症的抢救和治疗工作30年。近年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,参编医学著作5部。目前担任首都医科大学急诊医学系务委员、北京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、北京医学会灾难医学与心肺复苏分会委员,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急诊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,北京医师协会急救医学专科医师分会理事。
急诊科的大夫见到什么样的病人都不奇怪,但我第一次见到徐波(化名)的时候,还是被惊到了。眼前这个不到50岁的男人,骨瘦如柴,脸色惨白,1米7多的个子,体重只有70多斤。他躺在病床上,大口地喘着粗气,吸氧管插在鼻孔里,尽管氧气开到了头,但他还是觉得憋气。
即便如此,他仍然拼尽全力嚷着:“医院都不能吸烟吗?这是什么医院啊,我要回家,我要吸烟!”
徐波的病情很重,胸部CT显示双肺已经布满了结核病灶,双侧胸腔积液,还合并严重的细菌感染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也只能在兼顾抗感染的同时,进行抗结核治疗。
但徐波不太配合,每次扎点滴或抽胸水的时候,他都会大喊大叫:“太疼了,我不想活了,你让我死吧!”
更让医生头痛的是,徐波用不上抗结核的药物。几乎所有的抗结核药在他身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副反应——药物过敏、肝肾损害、视力模糊、粒细胞减少、血小板减少、末梢神经炎等。医生多次对他的疾病进行评估,肺结核、肠结核、结核性脑膜脑炎、结核性胸膜炎、重症肺炎、低氧血症、心功能不全、电解质紊乱、严重营养不良……这些病症全部纠结在徐波的身上,成为一根根压垮他的“稻草”。
其实徐波的家境还算优渥,父母都是知识分子,父亲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。但徐波自己却并不十分幸运,根据他的历史病历来看,他从小就是医院的常客。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,又得了鼻咽癌。好不容易在手术之后恢复得还不错,但没过两年,就又得了糖尿病。他一直单身,也没有工作,每天吸烟两三包。生活完全没规律,咳嗽咳痰一年多,实在难以忍受才来医院看病。
徐波的父母都80来岁了。每天,徐老先生开着车,带着老伴,从几十公里外的家驱车来医院看他。那时候正是新冠疫情期间,急诊科封闭式管理。老两口就相互搀扶着来到急诊门口,安静地坐在急诊的候诊椅上,等着大夫不忙了,跟他们说一下徐波的病情。但徐波的病情确实很重,我们跟老两口交代病情的时候,老太太总是泪眼婆娑的,不停地抹眼泪,总是自责地说是因为带儿子看病太晚了,才让徐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老先生表情凝重,但却不断地劝慰着夫人。两位老人家对我们医务人员总是彬彬有礼,对每一位大夫护士都以“您”相称,不停地道谢。
问完了病情,两位老人就走到急诊留观室的窗前,在那里伫立一阵儿,最后跟病房里的徐波挥挥手,两人再相互搀扶着离去。看着他们落寞的背影,我真希望能尽快将徐波的病情控制好,不要让这一对老夫妻失望伤心。
我跟徐老先生互留了联系方式,跟他们说:“我会每天跟二老汇报徐波的的病情,老人家们年纪大了,就不要天天来回跑了。”
之后的日子里,两位老人依然每天来到急诊门前询问徐波的病情。老太太说:“来医院,离儿子近些,心里踏实。张医生放心吧,我们一定遵守医院的规定。”
徐波拒绝转入病房,闹着继续住在急诊留观室里面。出于对他身体情况的考虑,再加上他自己的意愿,我们只能同意。虽然在多次尝试后,我们找到两个副作用相对较低的药物用于徐波的抗结核治疗,但对于这么重的结核病,康复之路依旧遥远且漫长。
然而,在治疗稍有起色的时候,徐波又开始闹着要出院,嚷嚷着医院饭不好吃,又是说天天打点滴受罪。以徐波当时的状况,根本离不开吸氧,如果出院,没办法保证后续会不会出现更糟的情况。
“我家里有氧气机,张医生,我跟你直说吧,在医院里面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要是这么也叫活着,真不如死了算了!”
见徐波一再坚持,医生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于是,给徐波准备了口服的抗结核药物,详细叮嘱了回家的注意事项。可是没过几天,徐老先生就给我打来电话,问我徐波又发烧了,还喘得厉害,应该怎么办。我一听便知情况不好,叫徐老先生马上呼叫120。就这样,徐波被送了回来,又成了我们急诊的病人。
回到急诊的他依旧如故,只要病情稍微好一点,就嚷嚷着要离开医院。如此反反复复三四次,半年时间过去了,徐波的肺内病变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善。这期间,我们也请结核科的主任一起制定了抗结核治疗的方案,但用药没几天,副反应又出现了,不得不停药减药。
一天夜里,我在家里接到值班医生的电话:“主任,徐波又来了,肺性脑病,血气二氧化碳分压130mmHg,人已经昏迷过去了,建议去ICU气管插管上呼吸机,但家属还在犹豫。”
我匆匆换好衣服,正准备去科里看看,徐老先生打来了电话。还是彬彬有礼,甚至有些谦卑地说:“张主任,小波这回怕是挺不过去了,去ICU治疗,听说全身要插好几个管子,我不想再让他再受罪了,不抢救了,您说我这个决定对吗?”
一位曾在自己的领域里叱咤风云的老教授,面对自己唯一的儿子即将离去时,却是如此地无助。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或许即使上了呼吸机,病人也未必能救过来,或许即使这次侥幸逃过这一劫,未来也很难说。要康复确实太难了,很有可能最后人财两空。可就这么放弃一个不到50岁的生命,我总是有些不甘心。想起徐波的父母相互搀扶的背影,我不禁鼻子一酸,说:“老先生,如果现在不马上气管插管上呼吸机,徐波今天就熬不过去了,日后想起今天的决定,我们会不会后悔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,“我明白了,我现在就签字同意去给徐波插管上呼吸机,马上去ICU抢救。谢谢您,非常感谢!”
“我过去陪陪您吧。”我有些不放心,毕竟是80来岁的老人了,我怕老先生的身体吃不消。
“您明天还要上班,不麻烦了,我知道该怎么做了,您休息吧,打扰了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颤抖着,带着哭腔。但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时刻,这位老者依然在为我着想。
徐波在ICU里住了4个多月,每天我都会在医院的系统里查看徐波的情况。今天清醒了,今天气管切开了,今天体温正常了,今天消化道出血了,今天又发热了,今天胸片肺里的病变吸收了一些,今天撤机了……在漫长的四个月里,徐老先生经常与我联系,说一些徐波的近况,每一次的最后,都会不住地道谢。当徐波从ICU出院的那天,全家人又来到了急诊致谢。
同时,我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。结核科有了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,经过临床观察,效果不错,副反应很小。连同以前用过的两个抗结核药,为徐波的治疗组成了新的治疗方案。
奇迹出现了,徐波的病情竟然有了很大的改观。渐渐地,他每天吸氧的时间越来越短,饮食和体重也有所增加了。
去年年底,我突然想起,徐波已经有几个月没来医院复查了,我给徐老先生打电话,听说徐波最近已经好了很多。
听见自己的病人得到了好转,我比什么都高兴,但是为了以防万一,我还是提醒徐波可以到医院复查一下。
那一天,徐波来复查,依然坐着轮椅,我不免有些失望。已经治疗了将近两年了,还是离不开轮椅。徐波见了我,从轮椅上站起来走向我。我太惊喜了,两年来,我第一次看见徐波站在我的面前,此前他不是坐在轮椅上就是躺在病床上。
我问他:“好些了?”
“好多了。”
“还吸烟吗?”他不好意思地红了脸,连连摆手。
“现在天天在家干些啥?”我问。
“炒股,还小赚了呢。”我第一次看见徐波笑了,笑容灿烂得像个孩子。
最终,各项化验检查指标明显好转。胸部CT检查,肺内的病变也吸收了不少。
后来,徐老先生曾告诉我,“那天夜里,我真的慌了,不知道该怎么办,要不是您提醒我,如果不抢救,我就没儿子了。多亏您帮我下定了决心,不然我真的会后悔。现在我老了,儿子依然在身边,我和夫人很幸福。”

而我想说,是两位老人家对徐波的爱、对医务人员的信任,以及他们不计得失地放手一搏,才换来了徐波的生命。
徐波的病情在好转,但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在急诊的工作是忙碌的,也是幸福的。作为医生,每天都会有救治成功的喜悦,每天都会收获病人和家属的信任和感谢。也正是这份真诚的信任,让我如此感动,更是我努力前行的动力。
医学人文点评
急诊医生每天都忙忙碌碌,他们在与死亡赛跑,在与危重症博弈。但即使这样,没有任何一位急诊医生在急危重症面前会有十足的胜算。医学不是纯科学,高大上的技术也不是无所不能。徐波这位患者的病是急诊的危重症,在治疗上可谓一波三折,时好时坏。急诊医生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与疾病苦苦斗争。可最终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,渐渐走出危重症的阴霾,还是来自家属对急诊医生无条件的信任和尊重,使得急诊医生能够站在人的视角,把悲悯之心融入到每一个治疗的细节中。真正的医学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撑,更要有医患和家属之间在情感上彼此真诚互动。这种互动可以给双方带来意想不到的能量,也会给医学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。所以急诊医学的着力点一定要在人,而不单纯是病。
点评人:赵斌
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主任